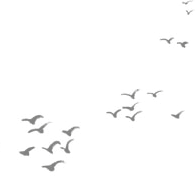【摘 要】水治理的“河长制”模式不仅满足了水资源的流动性、跨界性、产权模糊性以及治理综合性对治水提出的内生需求,而且破解了既往“九龙治水”导致“条条”和“块块”执行矛盾的困局。为将“突击式治水”转变为“制度化治水”,必须把本来无人愿管、肆意污染的河流变成悬在“河长”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通过实施“河长制”实现“河长治”,关键在于明确地方主官的纵向责任和横向责任,厘清上下游、左右岸、主干流地方主官间的责任关系,确保建构一套行之有效的“责任机制”、“协同机制”和“问责机制”。
【关键词】“河长制”;地方主官;水治理;责任
一、问题的提出及文献综述
2016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2017年新年贺词提到“每条河流都要有‘河长’”。不但将“河长制”再次带入公众视野,而且为地方水治理研究提出了新课题。
发轫于江苏无锡太湖蓝藻治理的“河长制”,后经江苏、浙江、江西等地的实践证明,该制度不但可以破解“九龙治水”的困局,而且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取得较为显著的治水成效。对此,有人认为是“人治”行为,缺乏法律基础;有人认为是“突击式治水”,缺乏持续性;也有人认为是“官治”之举,缺少社会公众参与,等等。为将“突击式治水”转变为“制度化治水”,让本来无人愿管、肆意污染的河流变成悬在“河长”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不少学者提出了不少建设性的观点。
一是制度形态论。黄爱宝针对河长制属于人治抑或法治的讨论,基于社会治理模式演进的历史视野,认为“河长制”属于特殊的制度形态,其既不属于典型的权力制度及法律制度,又不属于典型的道德制度,却在不同程度上具有这三种类型制度形态的某些特征。因此,应将“河长制”定位为有序消解其权力制度特征,适度追求法律制度构建以及逐步强化道德制度建设,使其永久持续。
二是法律完善论。王灿发、任敏等认为应从法律制度体系对“河长制”进行完善。政府应该充当“守夜人”角色,通过河长制进一步厘清政府部门职责,完善规范运作,但有可能陷入协同治理困境。同时,苑清敏等针对“河长制”运行的不足与困境,建议对领导干部加强“法治”教育,在实现“河长制”法治化建设的前提下,保证“河长制”为河长“治”。
三是社会参与论。刘国翰通过浙江省“五水共治”实践的研究认为,由于社会河道治理比较复杂,既涉及城市建设也涉及公民素质,还涉及企业行为等问题,因此河长制需要社会共治。在赋予公民足够环境权能的基础上,建立制度化的公众参与渠道,实现水环境生态决策、管理、项目实施以及冲突解决等环节的参与,才能达到更好的治理效果。对此,王勇认为应尽可能提高公众的参与水平,建立公众参与和政府主导的有效联接,形成“多中心”的水环境治理结构。
四是技术治理论。也有不少学者在“网格化治理”的理念下,建议借助技术手段打造实时监控平台,以确保河长“治”。譬如,福建省大田县的“易信晒河”软件平台,将河长工作的“查”、“处”、“究”流程串联在一起,促进河长的工作规范有序开展。浙江省的“河长制管理信息系统”,借助统一的管理信息系统,消除信息孤岛,以确保河长治水的效果。技术治理要求科学配置地方政府水权治理的方向,动态检测水质变化,确保水质安全。
五是立体治理论。刘柏煊依据“污染在水里,根源在岸上”的逻辑,认为只有对河面、河底、河岸进行全方位、无死角的治理,才能保证水域治理的成效和持久。如,通过对河湖周边环境进行综合整治行动,确保“河岸清”。采用各种技术措施,清理河湖水面垃圾和有害水生植物,实现“河面清”。组织实施河湖清淤疏浚,并且做好相关监测工作,保证“河底清”。
上述研究奠定了本文的研究基础。囿于“河长制”的命题较新,既有研究对“河长制”的经验总结较多,学理研究较弱,特别是对“河长制”产生的逻辑及其关系—责任研究较少。事实上,早在2008年2月修订《水污染防治法》时,引进“目标责任”和“考核评价”两种制度,对地方人民政府及其负责人的水环境目标完成情况进行考核评价,便明确了地方水环境治理的责任主体。具体而言,“河长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责任主体——地方主官(党政首长)。为回答这些问题,本文拟从“关系—责任”视角入手,分析“河长制”治水模式产生的制度逻辑,挖掘“河长制”运行中遇到的障碍及其破解之道。
二、内生需求:
水资源的物理性与社会性共催“河长制”
“河长制”的责任主体是“河长”。因此,对于承担“河长”的地方主官(党政首长)而言,“河长制”的实质就是责任承包制。之所以要求地方主官承担治水之责,站在地方全局高度统领和统筹水治理,主要是水资源自身具有流动性、跨界性、产权模糊性以及治理的综合性等特征。
一是水资源的流动性。与相对固定的土地相比,由于自身的物理特性,水资源在地心引力的作用下,从高处向低处流动,形成河川径流,最终流入海洋或内陆湖泊。无论是水的自然流动,还是因为人为因素造成水土流失、洪水泛滥以及污染蔓延,都会因水资源的流动而使人与水、河流之间的关系紧张。为此,马克思指出,要协调这一对关系,“仅仅有识还是不够的,为此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
二是水资源的跨界性。自然界中所有的水都是流动的,特别是由于水的黏度(即流动阻力)很小,难以保持固定的自然形状,在自身重力作用下,向低处不断运动。中国河流跨界具有普遍性,由于国土地势的总趋势是西高东低,呈三级阶梯状分布,山脉纵横交错,地形复杂,气候多样,所孕育的河流不但数量多、流程长,而且水系类型多样。由此,形成众多跨县界、市界、省界的河流。国家统计局的调查结果显示,我国第一大河长江,流域面积占中国陆地面积的五分之一,流经19个省级行政区。
三是产权的模糊性。对于跨越县、市、省界的河流,无论是作为两地的分界线,还是从两地内部穿越,都难以界定水资源的产权。横跨两地的界河,多以河的中心线为分界线,即使通过技术手段对左右岸水资源的产权进行划分,但水体污染责任难以区分;穿越两地的河流,虽然有地理界限区分上下游,但对于水资源的产权难以清晰划分。也正是由于水资源产权的模糊性,不但致使市场失灵,而且导致政府失灵,甚至使相邻的两个地政府陷入“囚徒困境”,最终使水资源再现“公地悲剧”。
四是水治理的综合性。长期以来,中国治水的三大要务是防洪、农业灌溉和漕运。随着经济、技术和工业发展,人类生产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但是,“这样一来它就同时破坏了它自己的活动的条件。蒸汽机的大工业中差不多一切生产部门都需要比较纯洁的水。但是工厂城市把一切水都变成臭气冲天的污水”。因此,水污染、水生态恶化成为治水面临的新问题。水环境治理和环境治理一样是一项系统工程,需综合治理,同步解决水安全、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水景观、水文化、水经济等七个方面的问题。其不但涉及水利、农业、交通、地矿、电力、城建等国家部委,而且牵涉流域内各省市区县的相关部门。
由此可见,在日渐复杂的治水形势和严峻的治水任务下,“九龙治水”、条块分割、各自为战的治水方式难以奏效,亟需对治水方式和机制进行创新。地方主官作为责任主体,不但可以统筹因水资源产权模糊而产生的“分治”,而且可以规避或减少因水资源跨界而产生的“公地悲剧”。因此,水资源的物理性与社会性共同催生了“河长制”。
三、治理之困:
地方主官纵横职责的分担难题
长期以来,我国政府职能定位不清,水污染治理中经常出现中央和地方职责的交差、重叠,而且导致“条条”治水的“无责”和“块块”治水的“无忧”。地方主官治水的过程中,既没有为中央“分责”,又不能为中央“分忧”。
(一)“条条”治水:地方主官水治理主体责任的缺位
“职责同构”模式导致地方主官不用担责。由于受历史文化传统、国家的单一制结构形式以及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我国“不同层级的政府在纵向间职能、职责和机构设置上的高度统一”,并呈现出“自上而下”、“上下对口”、“左右对齐”的特点,即所谓的“职责同构”。在水污染治理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同时作为治理主体参与其中。但是,对地方政府拥有全面的、绝对控制权的中央政府,在水污染治理时实行垂直式(一竿子插到底)管理,不但难以建立有效的分层控制体系,而且造成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间的宏观调控与微观管理职能重叠。因此,在水污染治理时中央政府与各级地方政府之间的职责没有明确分解,不但造成政府间职责的边界不清,而且导致地方主官在水污染治理中即使没有尽职亦不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职责同构”的纵向政府间关系,使地方主官陷入“全能地方”与“无能地方”的困境。地方各级主官所面临的工作和任务虽与上级政府一样(全能地方),囿于其所掌握资源的权力有限(无能地方),不得不在“全能地方”与“无能地方”之间摇摆。特别是在“政绩考核”、“GDP考核”等指挥棒下,地方主官更多考虑如何进一步提升GDP、创造政绩,而不愿花太多精力关注水污染治理。即使在对水污染进行治理时,由于心有旁“骛”,很难做到尽职尽责。与此同时,在“双重领导、地方为主”的管理体制下,水污染治理涉及的水利、环保、住建、发改、国土、卫生、农业、经贸等诸多部门,既接受地方主官的领导,又接受各部门垂直领导;既要向当地主官负责,又要向垂直领导的部门负责。当地方出现水污染治理不力时,地方主官虽有领导之责,但其可将一部分责任推卸至涉水部门的垂直领导部门。因此,在这样的体制下,地方主官在水污染的治理中很难承担相应的领导责任。
(二)“块块”治水:地方主官水治理责任监督的失灵
虽早在198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就明确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辖区的环境质量负责,采取措施改善环境质量。2008年2月修订后的《水污染防治法》之第4条、第5条,不但规定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采取防治水污染的对策和措施,对本行政区域的水环境质量负责”,而且指出“国家实行水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度,将水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作为对地方人民政府及其负责人考核评价的内容”,地方主官理应承担各行政区域内水污染治理的责任,但由于河流界限和行政区界限并非重叠,常呈现“外溢化”和“无界化”的特点,地方主官的责任难以追究。
当同一河流流经不同行政区时,便产生“上下游”、“左右岸”、“主干流”等系列政府间在水资源开发利用和水污染防治方面的矛盾和冲突。地方主官为着重发展当地经济,处于上游的地方,不但大量拦截流水,导致河流水量锐减,严重影响下游的用水需求,而且对辖区内的河流进行过度开发利用,破坏河流生态,严重制约下游地方对河流的开发利用,甚至在“地方保护主义”思想的指导下造成地方的短期行为,以致形成地方政府间非合作博弈的“囚徒困境”。与此同时,我国“条块分割”性的管理体制,不但造成跨区污水治理的赔偿和污染责任归属等问题难解决,而且导致“上下游”、“左右岸”、“主干流”等地方间在地方利益协调、上下游生态保护以及补偿机制上产生新矛盾。虽然中央政府专门立法要求地方政府间协同治理水污染,但在跨行政区的水污染治理中,由于不同地方主官在价值整合、资源和权力分配以及政策制定和执行等三个方面一直存在“碎片化”特征,加之地方间信息流通机制、生态补偿机制不完善,以及法律法规、管理制度和技术操作等方面存在各种障碍甚至缺乏操作性,对于跨区域性的水污染问题,很难追究地方主官的责任。
四、“承包责任”:
地方主官的纵向职责的有效配置
2016年,水利部部长陈雷明确指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总河长是本行政区域河湖管理保护的第一责任人,对河湖管理保护负总责,其他各级河长是相应河湖管理保护的直接责任人,对相应河湖管理保护分级分段负责。河长制办公室承担具体组织实施工作,各有关部门和单位按职责分工,协同推进各项工作”。由此,形成以“主体责任”为核心,以“分级定责”和“分段定责”为两种主要形式的纵向水污染治理责任体系。
(一)主体承包责任
党的地方委员会是一个地区的领导核心,不仅担负本地区的全面领导,而且对水污染治理负有领导责任,党委主要负责人是第一责任人。同时,各级地方政府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和核心,必然要主动承担起水环境治理的主要生态责任,要求党政领导担任河长,依法依规落实地方主体责任。正如习近平在主持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上指出,“重点督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解决突出环境问题、落实环境保护主体责任的情况。要强化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的要求,对问题突出的地方追究有关单位和个人责任”。事实上,地方党政主要领导担任“河长(总河长)”,不但厘清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而且中央政府从宏观上行使对全国水环境治理管理、监督职能,有效地整合了本地相关涉水部门的资源。将涉水部门职责分工进一步明晰、责任边界进一步明确,按照流域水资源自然生态规律(流动不可分割性)统一协调管理,避免出现“管水量的不管水质、管水源的不管供水、管供水的不管排水、管排水的不管治污”的分割治水现象,打破了“环保不下水,水利不上岸”的尴尬现状,切实提升环境外部性下经济空间和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二)分级承包责任
《意见》要求全面建立的四级河长体系中,须由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以及县委县政府等地方主官担任负责人。由此组成的“总河长、副总河长、河长、副河长、河段长等”地方水污染治理组织体系,实质是在“职责异构”思想的指导下,厘清了地方各级政府的职责分工关系,区分了上级与下级的职责,实现了水污染治理区域和政府层级相对应,明确了水污染治理主体责任,避免了多层级政府治理同一水域、河段。如江西省,一方面按照区域与流域相结合的原则,建立起以省委书记为省级总河长、省长为省级副总河长、省级党政四套班子的相关7位省领导分别为“五河一湖一江”省级河长、省委组织部等23个单位为省级河长制责任单位的“省、市、县、乡、村”纵向五级河长组织体系。另一方面按区域划分的原则,任命11个设区市、100个县(市、区)的党委、政府主要领导为市级、县级总河长和副总河长。同时按流域划分的原则,又明确了88位市级河长、822位县级河长。《江西省实施“河长制”工作方案》将省、市、县三级地方河长的责任进一步明晰。如,“总河长”和“副总河长”主要负责总督导、总调度,其他各级“河长”则是所辖河流河湖保护管理的直接责任人。其中,所辖河流河湖保护管理工作的指导、协调由省级“河长”承担,本区域河湖水污染综合防治、河湖生态修复、突出问题整治、河湖巡查保洁以及河湖保护管理等具体工作,由负责属地责任的市、县“河长”承担;河长各项工作的有效组织实施与落实,由各级地方河长办公室负责协调。
(三)分段承包责任
鉴于行政区域与河湖流域不能完全重叠,《通知》要求“各河湖所在市、县、乡均分级分段设立河长,由同级负责同志担任”。事实上,分段承包责任将河长、河段长的水污染治理职责进一步细化、实化。通过分段治理、分段管理、分段考核、分段问责,便能促使每一段的“河长”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守土担责,以保证“河长制”的成效。如长江主要支流之一、江西省最大河流——赣江,流经赣州、石城、瑞金、会昌等46个县市区。为保证赣江水流域的污染治理效果,由江西省副书记担任“省河长”,赣州、石城、瑞金、会昌等46个县市区的县长、市长、区长等担任“段长”,共同构成赣江流域的污染治理承包责任体系。贵州省亦是如此,为治理三岔河流域环境污染,对其进行分段治理。与此同时,河长根据各河(湖)段的水情、当地发展水平以及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坚持问题导向,因地制宜、因河施策地进行分类指导。
五、“协同责任”:
实现地方主官的横向联动
为避免出现部门间水污染治理的“碎片化”、地方政府间因横向利益分配而导致的“保护主义”甚至“以邻为壑”等现象,《意见》不但要求对各方力量进行整合,以加强水资源、水域岸线管理的保护,以及水污染和水环境的防治与治理等工作,而且要求厘清各部门间在水污染治理中的关系与责任,分清地方政府间的关系与责任,通过联防联控实现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的统筹治理。
(一)部门横向协作责任
水污染治理综合性的突出问题是同一地区内治水部门林立,互不统属。如,对于同一条河,水利、国土、环保、林业、农业等部门便有不同的管辖权,部门之间权责不清、推诿扯皮现象屡见不鲜,虽有“九龙治水”,却治不了水。“河长制”将地方主官作为地方治水的第一负责人和牵头人,有效避免了部门“分治”带来的“冲突”与“推诿”。“河长制”的实施,实现了各职能部门明确分工、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承担相应的任务和责任。如发改、环保、水利、农业、林业等部门重点做好分管项目的落实和监督工作,国土部门要及时研究配套落实重点工程所需的土地指标,改善由于部门条块分割管理所导致的水流域生态、经济、社会效益不能同步发展的情况。
如实施“河长制”的江西省,分别由省发改委、水利厅、环保厅、林业厅、住房城乡建设厅、教育厅、科技厅、公安厅、省委农工部、省政府法制办、省卫计委等23家省直机关共同参与。最后形成省直部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协同配合,共同保障“河长制”顺利实施的机制。与此同时,江西省内的各市、区、县在实施“河长制”时,亦将治水部门进行分类指导,厘清关系、划清责任。如在乐清市,分别对市委组织部、宣传部、农工部、市编办、市政府法制办、财政局、审计局、考评办、城管大队、规划局、环保局、乐平工业园区、金山工业区管委会等28家单位的工作职责进行明晰,协同治水。
(二)地方横向联动责任
由于河湖上下游、干支流所经地方不同,左右岸所属行政区域不同,以及同一地方内不同行业的利益不同,常导致河湖系统管理保护工作成效较差。为此,《意见》特别要求“对跨行政区域的河湖明确管理责任,协调上下游、左右岸实行联防联控”。在“河长制”中建立地方政府间(省、市、区、县)的区域联动机制,不但破解了流域生态环境的整体性与行政区划的碎片化之间的矛盾,而且避免了地方间在流域治理上不配合、不协调的现象,还将形成水治污治理的合力。
事实上,为实现地方间的横向合作治水,我国先后出台了与流域水污染联合防治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文件。如《水污染防治法》(2008年修订)之第5条、8条、15条、28条、56条分别对流域水污染联合防治的体制、制度和机制做了原则性规定。2011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要“进一步完善水资源保护和水污染防治协调机制”。2012年环保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水利部联合出台了《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2011-2015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提出“建立污染防治区域联动机制”。在省级地方政府间,先后创建和完善了松辽水系保护领导小组及协作机制、黄河流域突发水污染事件信息沟通与协作机制、桂黔跨省(自治区)河流水资源保护与水污染防治协作机制以及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区水资源保护和水污染防治联席会议制度等;在省级地方政府内部,由于存在共同的上级人民政府,即使在不同的市级和县级地方政府间,亦可统一地方责任。如,在统一核算流域环境容量的基础上,对各行政区域和各行业的水污染排放总量进行分配;对于水环境质量超标的跨界断面,上游应当按照统一标准对下游支付污染损害补偿;对于水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的跨界断面,下游应当按照统一的标准向上游支付生态收益补偿;对于发生在跨区域的水污染事故,通过行政区域间监督作用的发挥以及区域责任追究机制的建立,使区域联动责任真正得到落实。
六、结论
在“治国必先治水,水治才能兴邦”的中国,长期形成了中央高位推动下的“统领型水治理”与基层丰富的“合作型水治理”,但却造成地方水治理的“虚位”。因此,《意见》明确指出,“全面建立省、市、县、乡四级河长体系。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总河长,由党委或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担任;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内主要河湖设立河长,由省级负责同志担任;各河湖所在市、县、乡均分级分段设立河长,由同级负责同志担任”。本文从地方主官责任的视角,对“河长制”进行深度剖析发现,“河长制”的实施不但激活了地方主官的责任意识,而且有效地破解了地方“虚位”困境,形成地方主官的“定责型水治理”模式。由此,与中央高位推动的“统领型水治理”模式和丰富多样的基层“合作型水治理”模式共同构成极富中国特色的三级水治理体系,并凸显地方治水的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地方治水的核心在“定责”。过去的治水逻辑是:鉴于水域与行政区划不一致,根据管理的不同需要建构起“九龙治水”的治水格局。然而,“九龙治水”不但造成多头管理、职责不清和权责不明,而且治理效果差。“河长制”找到了地方治水核心,即“定责”。通过定责,不但厘清了职责、统一了权责,而且通过实施追责,将“责任”落地,治水成效显著。
二是河长制的本质是“主官责任”。从某种意义上说,“河长制”的本质上便是“定责制”。通过实施“河长制”,不但落实了属地管理的责任,而且抓住了治污的源头。河长制之所以在短期内取得显著成效,究其原因在于“定责制”以利益制约为机制,以责任为核心,不但确定了地方与国家之间的责、权、利关系,而且明晰了地方主官的“责任”。为切实履行责任,地方政府要统筹相关部门、协调不同方面的利益,加强环境监督,落实财政预算的公共支出。
三是河长制的关键是“责任机制”。作为河长,不但需要知晓河长的使命,而且承担相应的责任。如省委省政府一把手领导,承担总河长责任,市县领导承担河长责任。河长不但接受相应工作职责约束,而且受到系列责任机制的约束,对生态环境经济损失加以评估。实现道德责任、法律责任、政治责任、行政责任以及党委政府水治理的主体责任和党政主要领导承担水治理的第一责任的统一。
四是河长制的保障是“问责机制”。面临“失责”,便需要“问责”,甚至“追责”。为切实落实河长制的责任,鉴于河长的特殊身份(党政一把手或主要领导),便需要通过党内问责、行政问责、司法问责、人大问责以及公众问责,督促其认真履责,最终实现长效治理。
【注:限于公众号的篇幅限制,省略了参考文献和注释,但不影响读者理解原文】
原载于:《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第13-18页
本文作者:郝亚光,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政治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施佳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