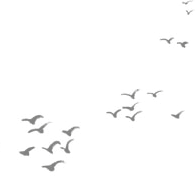章开沅先生
记者:那么您是怎么想到要去要研究苏州商会的呢?
马敏: 我走上商会史研究的道路也是一个机缘,这也得归功于章开沅先生。上世纪80年代初,有几位学者到苏州去,苏州档案馆的同志很热情地拿了一些商会档案给他们看,想让他们评判这些材料的价值。结果可能有些先生没有认真研究,就说苏州商会是一个很小的商人组织,没有太大的研究意义,不值得花大功夫去整理。但当时整理档案的骨干叶万忠先生很不服气,他认为苏州档案馆最有价值的就是商会档案,而且商会档案还很有系统。恰好章先生当时到苏州去,叶万忠就请章先生再看看,如果他也说没什么价值,那就把这些资料封存起来。章先生一看,非常兴奋,认为这些档案非常有价值,简直就是苏州近代商人组织的活化石。你想,从1905年一直延续到工商业改造的1956年,这么长的历史时段,完完整整保存下来的上万卷的档案,涉及到苏州的方方面面,能没有价值吗?
章先生回来后就在一节本科生课堂上(当时我没有读研究生)和我们讲,他最近在苏州看到了一批材料,觉得这批材料很值得研究。他说,我们通常都在讲法国巴黎公社,但其实苏州当时有商会,还有市民公社。如果深入去看这些档案,就会发现就活动程度组织能力而言,苏州商会绝不比法国革命前那些市民组织差,而且商会是研究辛亥革命中资产阶级性质的一条线索。
我当时听进去了,所以我下决心去考章先生的研究生。记得是1982年春,考上研究生后,章先生派给我们的第一件事,就是让我和朱英教授跟着刘望龄老师去苏州,参与苏州商会档案的整理和编纂工作。在苏州一待就是大半年,都在整理档案。后来又经过了几年夜以继日的劳动,我们编选出了长达120万字的《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一辑)》。
从整理苏州商会档案开始,我才算真正进入了商会史研究领域。我和朱英教授合写的《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就是基于这些珍贵档案材料。从1982年到现在,我们终于把这些商会档案编出来了,现在华师出版社出版了6辑12册,还差1辑。如果全部出来,那就是7辑14册,1000多万字。做学问是很不容易的,《苏州商会档案丛编》是我们前后历经30余年,靠着几代人的努力才弄出来的。我们前不久出版的四卷本《中国商会通史》,前后也用了六年多的时间。这套书是很大部头的,而且很系统,今后研究商会是绕不过它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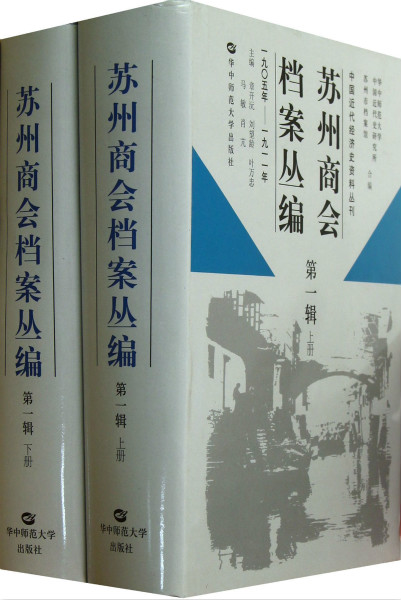
《苏州商会档案丛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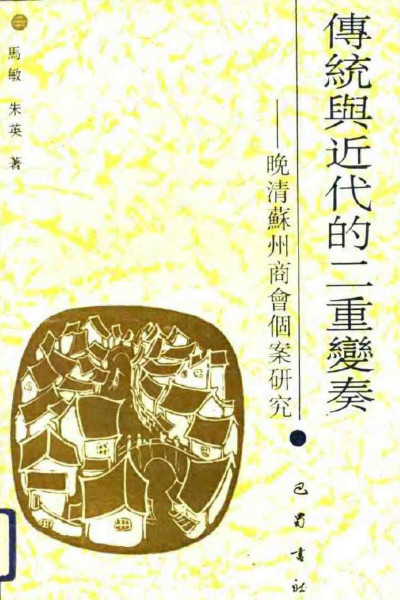
《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
记者:商会档案材料这么多,涉及到商会的方方面面,您重点关注的是哪些部分?又是怎么得出您的研究成果的?
马敏:对研究者来说,如果你遇到了一些好的资料,比如一些系统的档案材料,你可能算进入了与这些材料相关的研究领域。但即使接触了很多这么好的商会档案史料,能不能做出好的研究是很难说的。有的人接触了很多非常好的材料,可能仅仅把那个材料整理一下就出版了,最后只是一个很肤浅的东西,不一定很有水平。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就需要动脑筋,把笨功夫和活脑筋结合起来。
我的体会是,要对商会档案进行解剖,对商会组织系统本身有一个很深入的了解。有的人理解很简单,研究苏州商会就只研究苏州,研究上海商会就只研究上海,而不去考虑这中间有哪些组织联系。我们就不一样,当时系统论很热,我们对系统论也不是很了解,但是对系统性思维的方法很感兴趣,于是我们把它引入史学研究,在具体的研究中去发现其中系统的联系,以一个大的系统架构来把握它。就这样,通过对商会组织进行解剖,发现它自身有一个组织系统,有总会、分会、分所,从中心城市一直到下面的乡镇,是一个网状组织。
另外它自身又通过与各地商务总会的连接,形成了地区性、区域性的网络,比如说上海商会联合会,它的网络是从地方到全国的。由此,商会从乡镇到城市,再到一个区域,又到全国,再发展到海外。把商会研究推向海外后,发现它还有更大的一个系统,就是海外各地美洲、南洋等也都散布着商会。
近代商会、绅商与辛亥革命
记者:近代商会在城市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马敏:商会存在于城市中间,不管是大城市还是小城市,它都跟城市、社会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城市中间扮演了重要角色,涉及到城市的经济、政治、社会、公益、教育多方面。商会是一个活化石,能帮助我们去了解中国近代城市是怎样发展的。
美国有一个著名学者叫罗威廉,他最成功的研究之一就是汉口城市研究,还就汉口写了两本书:《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1796-1895)》。这两本书是城市史研究的权威性著作,他也因此获得了费正清奖。罗威廉是从商业组织跟城市发展的关系入手,一步一步地将汉口研究透了。他找到了很多有用的资料,当然还有很多海外的资料,当时我们很奇怪,我们去研究汉口,总是感觉找不到资料,结果他写了两巨册关于汉口的书,资料非常丰富。实际上他就是从行会、城市生活入手,把城市的组织和社会功能联系起来做研究,在汉口研究上取得了很大的突破。
我们研究商会也是类似。如果仅仅就研究一个商会,你讲得再清楚,也就是一个商会,但是如果把苏州这个城市讲清楚了,那就不得了,因为苏州是很有代表性的中国城市。上海是殖民者建立的一个飞地,是受西方影响很大的租界,而苏州则是自己发展起来的中国古典城市,当然它也受到了西方的影响,但是影响比较小。所以在几十年前我就做出一个预言:如果某一天苏州找到了它的发展道路,那么它的发展速度和发展能量会是惊人的。当时大家都不相信,这样一个古老的城市能在现代化和工业化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吗?30年过去了,我们再看看苏州,它的发展速度是惊人的,已经把我们武汉甩在了后头,无论新城老城都发展得非常之好。当时我的判断依据是,明清时期苏州出了很多状元,文化很发达,是一个智慧城市,另外它建立了很多传统的社会组织。如果将这些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再和现代嫁接,它的生命力将会很旺盛,比起一些半殖民地城市,它绝对有文化根底和后发优势。
苏州之所以在近代发展得非常好,还在于它有一种自我协调、自我组织的能力。苏州有深厚的文化传统,也有一套管理经验,这套经验将官方组织和民间组织结合起来,形成了一套很好的“社会自组织”管理系统。社会自组织依赖于像商会、公馆、公所、教育会等社会组织,它们和官衙相互配合,把一个城市治理得非常好。
例如粪便问题。当时苏州没有像西方那样的厕所,只有马桶,但它的城市卫生体系却很完善,到了收马桶的时间,大家全部搬出来放好,然后车子来收走,弄干净再送回来。什么时候晒马桶也是井井有条,那么多马桶不感觉到臭,这是很不简单的。还有苏州的水道怎么维护?老人、流浪者怎么救助?它都有一套。
这些自组织里面有绅商存在,他们受了很好的教育,知道怎么从公众的角度来管理一个城市。当时苏州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既有官衔又经商,既有知识又有钱,成立了很多组织,不仅是商会,还有其他的社会组织。我觉得整个中国近代社会是过渡性的,绅商就是典型的过渡社会的过渡阶层。这些人既能稳定社会又能拿到官方资源,既有财力又有功名,既有传统的社会资源,还能学习西方知识,所以他们在城市治理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记者:绅商是怎样一个群体?
马敏:绅商是历史文献中的一个词汇,但它是绅士和商人的集合?还是特指一类人?这个问题我思考了很久,后来越来越觉得它可能特指一类人,例如绅商王某、绅商张某,这说明“士人”和“商人”两个名词已经集合成一个名词了,绅商成了一个很紧密的群体。
绅商就是辛亥革命时期所谓的资产阶级。中国式的资产阶级就是这些人,既是官又是商,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站得住脚,如果仅仅是没有官方背景的生意人,没人理你的;但仅是官员而没钱,也干不成事,在当时把权和钱结合起来才能做出事业来。
发现这个秘密后,我发现辛亥革命起义前各地都是这帮人在活动。为什么起义后局面能很快稳定下来呢?就是这些人希望尽快安定秩序。他们有商团武装,辛亥革命后,这些商团武装在城市巡逻,这样社会秩序就安定下来了,所以辛亥革命背后起作用的主要就是这些人。把这个群体弄清楚了,也就能理解中国近代城市社会发展的秘密,以及辛亥革命为什么很快就成功了,又很快失败了——因为这些人不再配合了,一旦社会秩序稳定了,他们就支持袁世凯了,在他们看来,袁世凯代表了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权力,所以他们支持袁世凯,反对孙中山,因此又引发了“二次革命”的爆发。通过绅商这个阶层,我们可以理解近代史上绝大部分的中国革命。
近代社会的大变局及重商主义的兴起为晚清绅商群体的出现创造了历史条件。晚清的绅商群体有商人向绅士的转向,也有绅士向商人的靠拢。绅商阶层里面又可以划分为士人型、买办型、官僚型三种不同的社会类型,这种划分反映的正是绅商这个群体的多样性,因为他们和不同的社会阶层相互接触、融合,也影响到了不同的社会群体。
绅商可以算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早期形态,之所以说是早期形态,是因为绅商还不是成熟和完备形态的近代资产阶级,而只是在中国社会由古代农耕社会向近代工商社会转变过程中,一部分亦绅亦商的人逐步向符合近代要求的企业家过渡,然后慢慢具备了近代民族资产阶级的某些思想和行为特征,构成了近代民族资产阶级的重要主体。
作为新的社会阶层,绅商具备了丰富的社会功能。他们不仅热心参与社会公益、博览会等事业,而且在以商会为核心的新式商人社团的兴起与整合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不仅如此,在抵制美货收回利权、立宪运动、辛亥革命等一些近代重大政治活动中,我们都会发现绅商积极而活跃的影响。绅商是近代中国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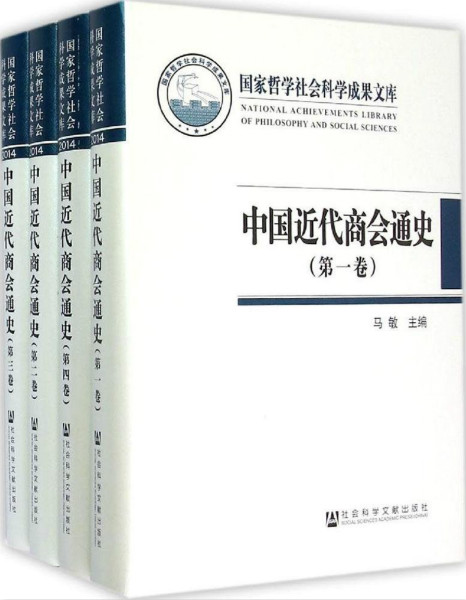
《中国近代商会通史》
学问不能关起门来做
记者:回顾您的商会研究,您有哪些研究心得和体会?
马敏:严格来说,我的学术研究是在跟随章开沅先生攻读硕士、博士后才真正开始的。说实话,能在丰富的档案史料中发现这种大小适中且极具发掘内涵的课题,已使研究有一半的成功把握,剩下的就在于自己是否勤奋、是否善于独立思考了。我在整理商会档案的过程中逐渐领悟出,对晚清亦官亦商的绅商群体的研究,可能是理解晚清商会构造和功能的关键点,推而广之,绅商研究也有助于探讨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就这样一个简单的领悟,使我在绅商和商会问题的研究上辛苦跋涉了整整十年,由而立之年步入不惑。十年的勤劳辛苦,加上大量的史料分析,以及经常性的思考,才有了这一点点研究成绩。
所以说,做学问真的是不容易的,需要长期的循序渐进、执着追求。那些真正学有所成的一流大师巨匠,没有一个不把自己看作“文化托命之人”,基于强烈的敬业精神,浓厚的学术兴趣,穷年累月,孜孜以求,全身心地关注一个领域,投入一项课题,最大限度地占有资料,反反复复地加以研讨,最终才形成独具一格的研究成果。著名的文献学大家张舜徽先生就是这样的典范。他在“文革”的时候,住的是澡堂改成的房子,环境恶劣,但是仍旧不分酷暑严寒地刻苦治学,日积月累地写成了200多万字的巨著《说文解字约注》,光毛笔就写秃了50多支。
学术研究是“由冷而热”的过程,开始都是冷门,但是随着研究不断地深入,也会慢慢“热起来”。当初我也没想到教会大学史能够成为一个热门,商会史现在也成为了显学,博览会史更是一个全国都在研究的领域。同时,我还要提倡“由热而冷”,这个“冷”是冷静,即在研究“很热门”的时候,要静下心来,深思熟虑,要充分利用“热”的时候流传出来的资料进行深入研究,而不是在这时什么都往外抛。
我觉得学术研究一定要有一个比较宽广的知识基础,并形成较为宽阔的学术视野和恢弘的气度。过去讲“文史不分家”,讲学问中的“通识”,均是强调知识的交叉性和渗透性,只有那些保持广泛兴趣的人,在相关领域都有所涉及、出入自由的人,方可做出大学问。一个人的知识、积累的材料也会影响一个人的研究取向。回顾过去三十年的学术生涯,我的主要研究领域(商会、博览会、教会大学)就是一个不断扩展的过程。学术研究有时候是带有偶然性的,不是说想研究什么就研究什么,有时候你想走进这间房子,却不小心走进了另一间房子,就像在树林中散步一样,突然发现一片开阔地,豁然开朗,学术研究也是这样,但是要善于发现,思维要开阔,要有开放的心态,这样才能从一个领域不断地扩展到另一个领域。
记者:您的研究是如何结合国外的理论,并与国外学术界展开对话的?
马敏:学问不能关起门来做,还需要与国际接轨。要把自己的研究纳入国际主流渠道,要能够和别人展开对话,如果无法与别人展开对话,自己说自己的,别人说别人的,这就叫学术不入流。这实际上也关系到我们商会研究的现代意义。
现在国外史学界普遍关注的就是市民社会问题。西方认为封建王朝结束后,在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中间有一个市民社会,在这个市民社会的基础上,资本主义社会一步一步成熟和完善。而在市民社会之前,还存在一个公共领域,哈贝马斯等人就提出,西方经历了从公共领域到市民社会再到公民社会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如果说我们的研究能和这些理论对话——当然不是说完全同意这些理论——但只要能够对话,实际上就把研究引向了国际史学的高度,别人才会认为你的研究有意义。
在20世纪90年代初,西方关于公共领域、市民社会的理论讨论得很热烈的时候,我们参与其中并进行了讨论。在做苏州商会与绅商研究时,我自己发明了一个名词,专门用来形容苏州的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叫做“在野的市政权力网络”。所谓的“在野的市政权力网络”就是很多社会组织连接起来的网络,这套网络或是与官方机构对立,或是与官方机构相配合,就这样形成了苏州的城市民间社会。
后来我一想,西方史学家说的不就是这么回事吗?西方在资本主义社会建立之前同样存在一些公众领域。西方讲的是咖啡馆、酒吧、舞厅等,我们没有咖啡馆,但有茶馆;我们没有舞厅,但有戏院。无论是茶馆还是戏院,都是公共领域,大家在里面可以欣赏到很多公共的东西,也是公共生活。西方史学家还提到了公共场所的议事,其实苏州商人所谈论的可能比西方还要广泛,他们不仅仅是在议事,还议论到枪杆子。苏州商团是有枪的,而且像民兵组织一样要巡逻,负责城市治安,保护商人的商业利益。很多纠纷和诉讼都是由商会来审理的,先是调解,调解不了再裁判。这些事例说明我们早期形态的市民社会,实际上比西方的市民社会内容还要更丰富,涉及面更宽。
从我们对晚清苏州商会的研究可以看到,晚清商会组织已经把自己的影响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以商会为核心,众多民间社团组织纵横交错,从而形成一个官府以外的在野城市权力网络,控制了相当一部分市政建设权、司法审理权、民政管理权、公益事业管理权、社会治安权,以及工商、文教、卫生等多方面的管理权,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城市经济和社会生活。如果不拘泥于字面意义的话,我们完全可以将此在野城市权力网络称之为“公民社会”的雏形,其背后的推动者,则正是新兴的近代资产阶级。
这样一想,其实中国也是有市民社会的,只是当时我们叫做市民公社。所以我觉得他们说的市民社会我们中国也有,但又不完全一样,它具有土生土长的中国特点,但是和西方的市民社会也有接近的地方,所以后来谦虚一点,我把它叫做“市民社会的雏形”。很可惜这个雏形没有发展起来,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这个市民社会就被压制下去了,到后来,蒋介石的党国更是一竿子插到底。
所以说我们的商会研究是有现代意义的,而且也能和国际学术接轨,这种研究才能算是有国际水平的研究。我们已经做了很多非常成功的研究,通过与别人对话,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找到属于自己的一套理论解释并且有事实依据就行了。说简单一点这就叫中国道路、中国特色。把自己的研究搞清楚了再去和国际接轨,就容易得多,怕就怕你没有研究就去和别人接轨,这样你就和别人谈不下去了,或者接到别人的轨上去了。
(本文系青年史学家“中国历史学教授口述历史计划”成果)